
李治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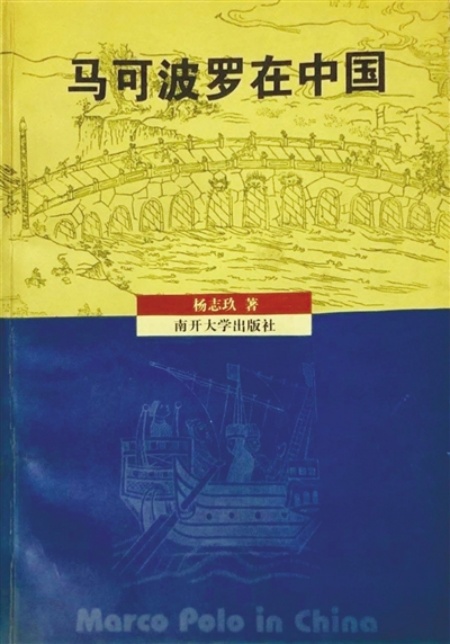
杨志玖先生的代表作
今年是杨志玖师诞辰110周年。忆起40多年前在杨师膝下亲炙教泽,入门读史,逐步成长的往事,总不免浮想联翩,感念不已。
我生性愚钝,“文革”后期当过9年工人,学业长期荒废。1978年,恢复高考的第二年,已满29周岁的我,才凭着“老高一”的那点儿基础,考入南开大学历史系。师从杨志玖先生学元史,说来也有几分偶然因素。大学三年级时,我原本想报考杨先生隋唐史专业的硕士生。不凑巧,1981年,先生中断了隋唐史专业招生,改而开始招收元史专业的硕士。不久我被录取,在先生的指导下开始学习元史。
先生曾不止一次对我们讲过:认真阅读原始资料,从中发掘许多有用的东西,所谓“如入宝山不空归”。单读后人以及当代人的著作,等于开百货商店,纵然货架上琳琅满目,却不是自己的产品,只能做个转手商贩。而我们做学问的,却要开工厂,亲自发掘原料,制成商品,供人使用。遵循先生的指教,我逐字逐句精读了《元史》、拉施德《史集》等基本史书。
记得是硕士第一学期末,我向先生汇报了阅读《元史》的进展情况。先生给我布置新作业:在一般阅读的基础上,做一份《元史·本纪》的大事记。我遵命行事,摘抄汇编了2万字左右的大事记,让先生过目。先生没多说什么,作业算是完成了。当时没有电脑,全凭手抄,花费了十天左右时间,很是辛苦。先生嘱我做《元史》本纪大事记,实乃从精细研读基本史料出发,学会“自办工厂”制造科研产品的早期演练。
针对元史专业对蒙古语等多种语言工具的依赖,先生还格外强调学习蒙古语等语言文字。读硕士之际,先生特意延请毕业于北京大学的包文忠老师(蒙古族),为王晓欣师兄和我开设了两个学期的蒙古语课,让我们接受比较正规的蒙古语训练。又写信向内蒙古大学乌兰老师索要《蒙古语入门》的教材,供我们使用。前一学期,只要先生不外出开会,几乎都和我们同时听课。看到先生年逾花甲依然认真地听课记笔记,我们自然不敢怠慢松懈,鞭策自己加倍努力学习。先生还要求我们到中文系听音韵学的课,我们遵命而行,适时增加了语言音韵方面的训练。
现在回想起来,杨先生克服种种困难,要求和鼓励我们尽可能多地学习掌握蒙古语等语言工具,恰恰是为我们研读史料“自办工厂”扫除语言障碍,故而非常及时和必要。
杨先生一生所写短文章居多,长篇大论较少,撰文言简意赅,甚至有些惜墨如金,从不说废话和空话。史学著述尤以重复他人旧说为耻。
我亲自聆听过先生有关考证马可波罗来华的讲演,也不止一次拜读先生发表于上世纪40年代的成名之作《关于马可波罗离华的一段汉文记载》,从中获益匪浅。诚如蔡美彪先生对我谈及的,杨先生等高明学者并非热衷于发现什么珍本善籍或罕见史料,而是能够立足一般常见史料,慧眼独具地发掘其隐微蕴意而做出好文章、大文章。此文正是运用常见史料做好文章、大文章的典范。元《经世大典·站赤》至元二十七年的那段百余字的公文,载于《永乐大典》卷19418。治史者稍作翻检,即可找到。然而,百十年来,谁也没能揭示此篇公文里隐藏着马可波罗离华的重要信息。先生之文的高明之处,就是基于多年来对于“回回人”的资料积累,紧紧抓住了“沙不丁”等四五个人名和“取道马八儿,往阿鲁浑大王位下”等关键字句,然后和《马可波罗游记》、拉施德《史集》等相比对,条分缕析,巧思发微,进而得出马可波罗1291年初自泉州离华的精彩结论。
上世纪80年代中叶,我在杨先生指导下开始攻读元史方向的博士学位。是时,更注意以先生的文章作楷模,广泛占用原始资料,巧思发微,努力捕捉题目并解决一些疑难问题。
先生一生的元史研究主要集中在探马赤军、“回回人”和马可波罗来华三大课题上。其代表作《元史三论》,依实际内容即得名于此。先生治学的涉及面虽不算太宽,但无一不是元史研究领域的前沿或争论热点,无一不处于国内外领先水平。目前学界风行“十年磨一剑”之说,先生则是一生磨砺三剑,平均二十年磨砺一剑,剑剑都精妙超人,令人叹服。受先生的熏陶,我近40年的元史研究选题,同样采用集团性探讨的方式。
先生精于考证,一生治学以考据见长。他的考据,祖述乾嘉,大部分考据论文把乾嘉方法运用得炉火纯青,且能见微知著,以小见大,显著推进有关研究。部分文章又尝试兼收伯希和等审音勘同方法,往往能把二者结合起来,水乳交融,浑然一体。
以我的亲身感受来说,先生的考据文章中,《关于马可波罗离华的一段汉文记载》和《关于乌马儿任江浙平章的年代问题》,堪称乾嘉方法运用的代表。在这类文章中,先生习惯于先引用一段或几句基本史料,然后旁征博引,逐项排列证据,辨析真伪,层层剥茧,最终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元代的探马赤军》和《元代的吉普赛人——啰哩回回》实乃乾嘉方法与审音勘同方法融汇一炉的佳作。
先生曾批评史学论文严肃有余、欣赏性不足,主张融学术性、知识性、权威性于一体。即使是撰写微观考据文章,先生亦力求通俗易懂,雅俗共赏,做到语言清新流畅,如同向人讲故事一般,娓娓道来,亲切自然。反驳他人观点,先生则摆事实,讲道理,充分尊重对方,与人为善,从不用武断或尖刻的词句。在这方面的确是文如其人,折射出先生宅心仁厚的品德。
先生一生淡泊名利,率直诚实,高山仰止,有口皆碑。撰写考据性文章,先生总是坚持真理,有错必纠。在探索考订疑难问题过程中,一旦发现旧作有错误或不足,就毅然公开承认纠正,毫不掩饰。1982年,先生发表《探马赤军问题三探》,接受贾敬颜、黄时鉴论文的中肯意见,依据《史集》有关记载,纠正过去的看法,把五投下探马赤军的解释重新修订为五投下抽调部分军士所组成的混编军。
先生还有个习惯,所撰论文或初稿愿意寄送多位同行朋友,希望及时得到批评或材料信息方面的帮助并听到反馈意见,以丰富和改进自己的课题研究。上世纪80年代初,先生与日本学者萩原淳平争论探马赤军问题,是时“文革”已结束,他刚刚把研究重点自隋唐史转向被迫停顿多年的元史领域,外文等资料匮乏,国内蒙元史重要域外史料的整理翻译正在进行中;先生撰写《探马赤军问题再探》《探马赤军问题三探》等文之际,不得不向韩儒林、潘世宪、余大钧等师友求助。在这两篇文章的注释中,先生写道:“本文(萩原淳平《木华黎国王麾下探马赤军考》)承内蒙古大学潘世宪先生译出,特表感谢”;“此(《史集》俄译本)承内蒙古大学余大钧先生译示,特表感谢”;“此承韩儒林先生译示,特表感谢”等。这种实事求是,志诸文以答谢的做法,先生始终坚持。
先生如此行事,充分体现他虚怀若谷、不耻下问、从善如流的品格。从治学上讲,又可见先生严谨认真、实事求是的学术风范。更重要的是,能够使自己的治学开放而非封闭,虚怀而非自傲,能够在与同行朋友的不断交流、争鸣中前进发展。这也是先生晚年老骥伏枥,高水平论著接连问世的原因之一吧!
自1978年负笈南开到如今,已历47载。忆及当年先生学贯中西,笔耕古史,宏著三论,蜚声海内;津门雅会,研讨马可,中外咸集,盛况空前。吾等问学陋室,考辨求真,教诲谆谆,茅塞顿开;新春节庆,家宴招待,师生同席,恩重情深。
寸草知报春晖,弟子敢忘师恩?拜书短文一篇,以祭吾师冥诞一百一十周年。
(作者系南开大学讲席教授)
学人小传
杨志玖(1915-2002),山东长山县(今淄博市周村区)人。著名历史学家。193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西南联合大学)历史学系,先在北大文科研究所读研究生,后借调至史语所工作。1941年留南开大学历史系任教,历任副教授、教授、博士生导师。曾兼任《中国历史大辞典》主编、《历史教学》编委会主任、中国元史研究会名誉会长、中国唐史学会顾问、天津市历史学会名誉顾问等。曾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天津市第六、第七、第八届委员会常务委员。著有《隋唐五代史纲要》《元史三论》《马可波罗在中国》《陋室文存》《元代回族史稿》等专著。
原文链接:http://epaper.tianjinwe.com/tjrb/html/2025-05/16/content_143100_2179145.htm
审核:闫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