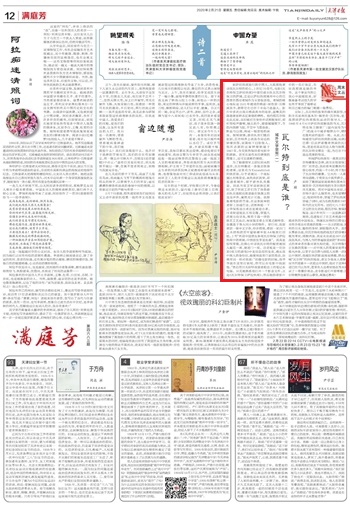
卢桢
到萨拉热窝旅行的中国人,大抵都抱着寻找瓦尔特的初心,上世纪70年代,电影《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中那位游击队长瓦尔特保卫的萨城,正是以萨拉热窝城市中心的巴西查尔西亚老城作为主要取景地。老城的核心地标是1531年建成的格兹·胡色雷·贝格清真寺,据称它在巴尔干半岛乃是最大。影片中多次出现贝格清真寺的场景,最唯美的段落便是钟表匠谢德的牺牲。他约假瓦尔特在此见面,当识破对方身份并试图脱身时,却听得枪声骤响,镜头抬升,谢德缓缓倒下,寺院内鸽群飞起,于空中飞荡盘旋,鲜血与白鸽,构成一幅悲怆的画面。按照剧情,游击队员们随后赶到,瓦尔特奔上清真寺旁边的钟楼顶部,居高临下扫射敌人。他所占据的这座钟楼始建于1667年,今天依然保持着电影中的原貌。甚至在某些未经修缮的围墙上,还可见清晰的弹痕。
为了躲避德军上尉比绍夫的追击,瓦尔特撤进一条售卖铁器的老街,这条名为Kazandziluk的铁匠街,位于老城另一个地标塞比利喷泉旁,虽然曲折狭窄,却连通着城外,便于游击队员撤退。因此当党卫军追到铁匠街时,除了听到工匠们为了协助游击队员逃脱而故意敲在铁器上的当当声外,竟然无计可施。我想象着电影的节奏,在这条狭窄的老街上加速行走,试图体验一下上帝保佑追击者还是被追击者,可老街道彼此互相克隆,穿插几次便方向尽失,唯有千篇一律的铁艺工艺品店,每家售卖着土耳其式咖啡壶、金属盘子等大同小异的物件。穿行间,我留意到一张中文字条,停步细观,看到一家店门上木结构的百叶窗贴着半张A4幅面打印纸,上书“欢迎中国朋友参观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中的商铺,中国朋友享受优惠”。我真是惊叹至极,仿佛心中寻找瓦尔特的秘密被别人窥见一斑,便进门一观。店老板是一位仿若《权力的游戏》中龙母造型的女孩,确认我中国人的身份后,她便用波黑口音的英语,仿佛背词一样对我说:“拍摄电影的时候,我爷爷就在这里打铁呢,你可以在电影中找到他。”然后用目光招呼我留意柜台上的笔记本电脑。只见她熟练地打开一个影音文件,正是《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然后她指着影片中的一位打铁匠,告诉我那就是她的爷爷。这个事实当然让我心中温暖起来,好像准备考试很久的学生终于等到了能够证明自己能力的偏门难题一般喜悦。
实际上,瓦尔特的故事的确有其原型,他的全名是弗拉基米尔·佩里奇·瓦尔特,是二战期间萨拉热窝抵抗运动的领导人。在1945年4月6日萨拉热窝解放的当天,瓦尔特在保卫烟草厂(国内误传为电厂)的战斗中被手榴弹击中,牺牲在胜利前的最后一刻。从此,瓦尔特被誉为萨拉热窝的灵魂,而演员巴塔·日沃伊诺维奇饰演的瓦尔特,更是将真实历史人物与银幕上的瓦尔特交缠在一起,为巴尔干缔造出英雄的传说。
听闻萨拉热窝有一座真实的瓦尔特雕像纪念碑,就立在他曾保卫的厂房旁边,我沿着米里雅茨河边留心找寻,约莫一个小时,终于发现了瓦尔特的雕像。它大约一人高,背向道路,于荒草丛中孤单矗立,上面除了雕刻国家英雄弗拉基米尔·佩里奇·瓦尔特和他的生卒日期外,再无其他。而对中国观众来说,瓦尔特不是什么佩里奇,也未曾牺牲过,他如同传奇,穿越了萨拉热窝,穿越了《桥》,成为东欧英雄和1970年代的文化符号。回归七八十年代之交的文化语境,假瓦尔特、智谋抓叛徒、设计炸列车……这些跌宕的剧情,迅速吸引了在艺术荒漠中饥渴求饮的中国观众。饰演瓦尔特的巴塔也完全符合观众对英雄的想象──方正的脸庞、锐利的目光、魁梧的身材、钢钳般的大手。虽然从事游击战,但瓦尔特和他的战友们的穿着却极为考究,绒制西装、真皮夹克或是007式的浅色风衣,与国人当时普遍接受到的“李向阳”式的革命者形象可谓大相径庭。瓦尔特般举止优雅的英雄──对中国人的英雄审美带来极大冲击,以至于当巴塔与剧组人员第一次抵达中国时,他被狂热的影迷围追堵截,群众高喊“瓦尔特”的热烈场面,着实令他本人费解。而当巴塔第十一次抵达中国时,他对于这种欢迎已经习以为常,甚至有人还看到他在秀水街买了一堆廉价商品,这令影迷们不禁唏嘘:瓦尔特竟然也要买山寨货,英雄迟暮矣!
http://epaper.tianjinwe.com/tjrb/html/2020-02/21/content_162_2331888.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