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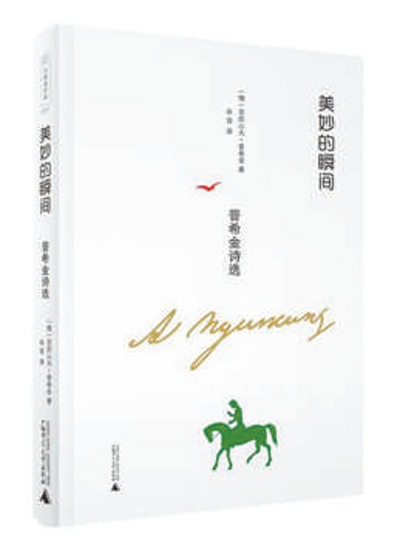
谷羽译《美妙的瞬间——普希金诗选》封面。

谷羽与谢尔盖·托罗普采夫合译的《李白诗读本》封面。
□谷 羽
我与俄语和诗歌相伴已有60余年光阴。从少年时踏入诗歌殿堂,到研究翻译普希金、蒲宁、巴尔蒙特等俄罗斯诗歌巨匠的作品,我在诗歌翻译的群山间不断攀登,留下深深浅浅的脚印。这些年来,我把重心放在中国诗歌俄译之上,获得莫大快乐。
结缘中国诗歌俄译
我与俄译中国诗歌的缘分可以追溯到一件小事。1988年11月,我到列宁格勒大学进修一年。刚到莫斯科,我与俄罗斯诗人彼得·维克托罗维奇·维根见面,问他读过哪些中国诗人的作品。他想了想回答说:“李白、杜甫。”我又问:“当代诗人呢?”对方愣住了,好半天才说出“艾青”的名字。
这次会面深深触动了我。中国俄语界翻译了不少俄罗斯诗人的作品,但俄罗斯当代诗人对于中国诗歌,尤其是现当代诗歌却所知甚少。在列宁格勒大学进修期间,我有意识地尝试反向译诗——将中国当代诗歌译成俄语并请俄罗斯诗人朋友加工润色。随后,译诗在当地报纸上接连发表。
回国后,因为忙于教学,又找不到适合的合作者,我将精力更多放在俄罗斯诗歌研究和翻译上,但心里却始终放不下中国诗歌俄译。2011年,我通过互联网结识了俄罗斯汉学家鲍里斯·梅谢里雅科夫和诗人阿列克谢·菲利莫诺夫。以此为契机,我重拾中国诗歌俄译,在大量阅读当代诗歌的基础上,选择40余位诗人的代表作,与合作者一同翻译成俄语。2018年,中国当代诗选《风的形状》俄译本在圣彼得堡出版,获得当地学者好评。
2015年,我开始和俄罗斯汉学家谢尔盖·托罗普采夫合作翻译中国古代诗词。两年后,《诗国三高峰 辉煌七百年》俄译本在圣彼得堡问世,选译唐诗、宋词、元曲近300首。俄罗斯著名诗人库什涅尔深爱中国古代抒情诗,他在前言中写道:“尽管中国和俄罗斯在语言、诗歌、诗歌传统方面存在种种差别,但也有不容置疑的近似性,我为此感到欣喜。”
我们的努力结出累累硕果。2020年,《汉俄对照中国诗歌读本》系列正式出版,读本共7册,收录了唐诗、宋词、元曲及20世纪80年代后的中国当代诗歌作品。这套丛书是我与合作伙伴对中国诗歌俄译的一次总结、修改和扩充,被列入“十三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获得国家出版基金的资助。
合译赋予诗歌新生
一首诗诞生后,即获得独立生命,它的生存与流传则依靠读者。诗歌经过翻译,被不同国家的读者接受、喜爱,正如破茧成蝶:在语言的转换过程中必然有所失去,失去的首先是语言外壳,和原有的声调。经过翻译,汉语的四声不复存在,但诗中的节奏和意象在另一种语言中再次呈现,令诗歌获得崭新的生命。
这个过程也是对译者的莫大挑战。我认为,中外译者合作向国外读者介绍中国诗歌是一种有效的方式。这些年来,我选择篇目,译出初稿,再由合作者按照俄语诗歌的特点和规律斟酌修改,做进一步诗化处理,从而得以在保持中文原诗风格韵味的基础上,便于俄罗斯读者阅读欣赏。经过近10年合作,我与不少俄罗斯朋友结下深厚友谊。
我和谢尔盖·托罗普采夫合作译诗已超过6年,谢尔盖为自己起名“谢公”,以此致敬李白推崇的诗人谢灵运和谢朓。谢公翻译的篇目,我是第一读者、评论者、鉴赏者和咨询者,我俩的意见常有分歧。他曾翻译李白的《赠汪伦》,把“踏歌声”译成了“音乐声”。为了修改这个词,我给他寄去了4个俄译本。他很快就回信给我,坦言这是多年前的译本,自己也不太满意。随后,译诗经过修改,面貌一新。他不仅确切地译出了“踏歌声”,还增加了地名“桃花潭”,音韵节奏俱佳。
我们也时常在切磋讨论后依然无法达成一致。翻译马致远的《天净沙·秋思》时,“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里的“小桥”,谢公译作“拱桥”。我和他商榷,从这首诗的意境判断,那应是个十分荒僻的地方,“小桥”可能是简陋的石板桥或木板桥,“拱桥”听上去更像修建在皇家园林或繁华之地。但谢公不同意这一见解,我也只好“求同存异”。
一首好诗,首先感动国外汉学家,他们通过翻译赋予它新的生命,让它展翅飞向远方的读者,飞向更加广阔的天地。宋代朱熹有诗:“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诗的传播与交往也如生生不息的活水,流进来,流出去,让世界诗坛多姿多彩,让读者的生活充满感动和喜悦。
与诗为伴六十余载
回首与诗相伴的60多年,我时时记得那些领我进门的前辈名家,他们的引导和鼓励至今历历在目。大学时期的俄罗斯文学选读课老师曹中德先生让我得以领略俄罗斯诗歌的美妙音响和真挚情感,并开始尝试译诗。系主任李霁野先生告诉我,文学翻译难,诗歌翻译更难。译诗需要精益求精,反复琢磨,一要对得起作者,二要对得起读者。李老的叮嘱,我一直牢记在心。毕业后,我结识了高莽先生,他主编《苏联当代诗选》《苏联女诗人抒情诗选》《普希金抒情诗全集》,都给了我翻译诗歌的实践机遇。我翻译的第一本诗集《一切始于爱情:罗日杰斯特文斯基诗选》,序言也出自他手。
1979年和1981年,叶嘉莹先生在南开大学两次举办诗歌讲座,我有幸聆听,并做了详细笔记。叶先生的讲座不带书本和讲义,所有诗词全都记在心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她的声音清晰悠扬,笑容平和优雅,每次听讲都是难得的艺术享受和精神洗礼。我至今还记得叶先生说:中文系的学生,国学根底比较好,但英语往往不过关;学外语的学生,外语不错,可国学根底比较薄弱。如果要研究外国文学,必须在这两个方面努力。这几句话为我指明日后的努力方向。
记录在两个笔记本上的160页叶先生讲课笔记,令我最为珍惜。2021年春节前,我整理房间和书籍,找到了保存完好的笔记本。开春后,我去叶先生家拜访,她精神很好,坐在轮椅上问我:“你今年多大年纪了?”我回答:“81岁。”叶先生说:“我都97岁了,你还年轻着呢!”这句话对我是莫大的激励。我给叶先生带去了与俄罗斯汉学家合作编选翻译的《李白诗读本》《唐诗读本》《宋词读本》《元曲读本》,叶先生回赠我一本她的口述史《红蕖留梦》。我回家后通读全书,深受感动。
回顾这些年来走过的路,我终于找到了俄语和最初渴望报考的中国古典文学专业之间的衔接点,并把两者结合了起来。外语是工具,文学是专业,诗歌是最爱。如今,我还在坚持读诗、译诗、讲诗,我始终坚信真正的译家不重声名,甘愿当架桥铺路工,陪外国作家“过桥”,伴读者“出国远行”。译者辛勤劳作求的是桥宽路平,也从诗歌中感受到美好和充实。
谷羽,原名谷恒东,1940年生。南开大学外语学院俄语系教授,天津作家协会会员,圣彼得堡作家协会会员。曾获俄罗斯联邦普希金奖章、安年斯基诗歌翻译奖、中国俄语教育终身成就奖等。主要著作有《帆船,在诗海上漂流——俄汉诗歌翻译研究》,以及《普希金诗选》《普希金爱情诗全编》等俄罗斯文学译著30余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