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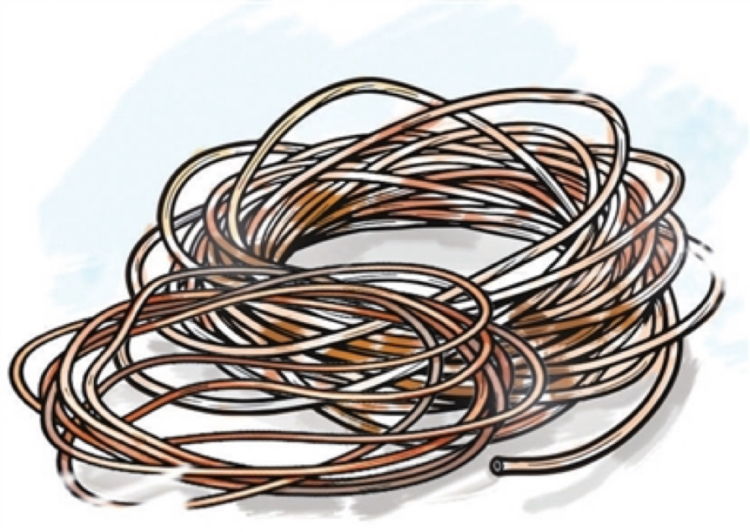 华 勒 题图 张宇尘
华 勒 题图 张宇尘
他19岁的时候已经独自在省城讨生活了。因为笃信“天干三年,饿不死手艺人”,于是,他跟一位同乡学做电工,从最简单的安装开关插座做起,每天忙得团团转,薪资也只够糊口。人愈穷胆愈大,为图方便,他经常带电操作,把身边的师傅吓得烟灰抖落了一地。
有一天,他问师傅自己还有多久才能出师,师傅笑着告诉他:“要想当师傅,有三个条件:一要怕死,二要有个不怕死的徒弟,三要知道铜的价格。”他以为师傅在开玩笑,气呼呼地扭过身子,低头猛干,心中颇为不满。师傅站在旁边像看一个顽皮的孩子一样,无奈地摇了摇头。
他22岁的时候,妻子生了一个男孩,八斤半,就出生在工棚的厕所。那天,他和工友在自己家里喝酒,喝到半夜,忽然听见妻子在厕所里大叫,冲出去看,才发现自己已经当了爸爸。众人这才慌忙拦车去医院。全凭妻子身心坚强,母子才俱得平安。他抱着自己的儿子,笑呵呵地对妻子说:“别担心,老板已经把过年的工钱预支给我了,连同过年这几天加班的津贴,我可以照看你坐月子,别担心。这小子命不错,生在工棚,一出生就有工作,不担心以后没饭吃。”妻子接过孩子,紧紧抱在怀里,眼里满是爱意。他看着躺在病床上虚弱的妻子,又看看浑身发红、闭着眼睛睡觉的儿子。突然间,他觉得自己开始害怕死亡了。
25岁那年,他已经能在业务上独当一面。这时的他已经明白了师傅当年那些话的含义。有了家庭就不再是“一人吃饱,全家不饿”,有了家就有了责任,就不是只为自己而活,就会怕死,就要想方设法多挣外快,补贴家用。“做哪行吃哪行”,电工的外快就在铜上。
有一次,他跟几个兄弟一起给一个老板装修宾馆,临时缺人手,老板便又安排了一个外地的小伙子和他们一起干。午休的时候,其他人都就地躺着睡觉,只有那个小伙子主动来找他搭话。那人颇为神秘地邀请他一起把地上不要了的废弃线头收集起来,看着他笑了笑说:“卖了,好给孩子买奶粉喝。”他心领神会,两个人不一会儿就捡了两三斤。线头是装修过程中产生的耗材,外皮是塑料的,里面是铜线,不加处理卖不上价,只有自己用工具把外层的塑料剥开,单卖里面的铜线才有得赚。那天下班早,他们两人一起加班半小时,把剥好的铜线塞进工具包,直奔废品回收站。
铜线一共卖了75块钱,两人平分各得37.5元,因为是小伙儿的主意,为表示感谢,他又另外给小伙儿买了一包烟。那时候,一斤铜可以卖35块,他一天的工资是25块。回家的路上,他看见路边有人推着小车卖汉堡,5块钱一个,他觉得有些贵,因为那时猪肉也不过七八块钱一斤。但他回到家的时候,手里还是揣了两个汉堡。那是儿子第一次吃汉堡,也是妻子第一次吃汉堡,他头一次觉得铜线是那么珍贵。
赚外快的日子,他始终提心吊胆,终究还是差点出事。他30岁那年,接到一单大活,给酒店装修。因为工程量大,所以业主派了监工。他干活的那几天,一直留意着把废弃的线头收集起来,他算准监工总是比工人早半个小时下班。所以,他理所当然地认为,只要等到下班便万事大吉。将好几天堆积的废料收在一起,满到连挎包口袋都盖不上,就在他满心欢喜地背着“战利品”下楼的时候,却发现监工正站在楼下,跟他迎面碰上,两人四目相对,场面无比尴尬。
他早就听说有不少甲方常常为难工人,一时间冷汗不住地从额头上冒出来。监工会不会直接向甲方举报,还是跟包工头告状,让他卷铺盖走人?难道要报警抓人?捡废弃的线头应该不算盗窃吧?一连串的问题比他额头上的汗珠冒得更快。
他甚至是带着祈求的眼神望向监工的,也许是希望能用这份真挚博得同情。可能是人到中年亦能理解养家的不易,让他意想不到的是,监工只是笑了笑,指着挎包对他说:“好嘛,这下你可要请我抽烟了。”他心领神会,长出一口气,不由得也跟着尴尬地笑起来:“抽烟,好说、好说!”监工就这样让他走了,以后也没有再找过他的麻烦。
35岁的时候,他第一次和儿子发生争吵。那天中午,他回家拿工具,准备去另一个工地收工。看见儿子并没有去上学,而是拿着一把美工刀在剥铜线。他问儿子,为什么不去上学,儿子说因为今天肚子痛,跟老师请了假,现在吃了药,已经好多了。说完,儿子骄傲地给他展示自己剥好的铜线:“爸,你看,足有一斤多呢,怎么样?”他突然大发雷霆,指着儿子的鼻子大声喊道:“臭小子!想做牛还怕没犁给你拉?没出息!有力气剥铜,没力气读书!”骂得儿子流着泪冲出了家门,留他一个人呆在原地。
他那天运气很不好,甲方对原本做好的地方不满意,只能重做,改来改去,收工变开工,一直加班加点干到半夜。等他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家,儿子已经睡了。
他推开儿子的房门,用粗糙的大手轻轻地抚摸着儿子,又给他盖好被子,这才关上房门离去。房间太黑,以至于他没有看见儿子紧闭着的双眼流下的眼泪。
他40岁那年,第一次跟儿子讲起有关铜线的一切。那天,为了祝贺儿子考上重点大学,他请了很多亲朋好友来家里吃饭,其中就有当年那个监工。他骄傲地把儿子介绍给自己的朋友。那天,他们喝了很多酒,工友们不断地向他道喜,他不住地说,全凭儿子自己有本事。父子俩头一次喝得酩酊大醉。他可能已经忘了,那天晚上他借着酒劲给儿子讲了很多故事,从过去一直讲到将来。他说:“我这一辈子就是做电工的命,但谁能想到一个小学文化的电工,能有一个考上985的儿子呢?爸爸就像那层铜线外面的胶皮,卖不上价了,可你以后要好好干,活出自己。”其实他不知道,在儿子的心中,那层胶皮比铜线更伟大。
(作者系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马克思主义理论专业2022级本科生)
原文链接:http://epaper.tianjinwe.com/tjrb/html/2025-11/06/content_143100_2792506.htm
审核:丛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