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叶嘉莹先生,摄于1997年11月(侯艺兵 摄,祝晓风 供图)
“百年闻至道,守孔颜乐处”,叶嘉莹先生是词中仙,更是天下士,她用百年人生写下古典诗教的诗篇,弟子门生遍布天下,皆因诗词而相会,她对亲传弟子更是极尽为师之恩泽,广赐德行之教诲。
叶嘉莹先生弟子汪梦川在文中追忆往昔叶门求学时的情景,讲述叶嘉莹先生对待弟子的如海雅量和殷殷期许,借此展现叶嘉莹先生令人钦佩的学术志业和人格品质,也表达其对恩师叶嘉莹先生的无限缅怀与追思。
我自二〇〇一年开始追随叶嘉莹先生,至今已二十余年。先生之道德文章,早已为海内外所公认,自然无须我置喙。而回顾在先生身边的日子,最令我感念者,就是先生如海的雅量和对我的殷殷期许。
我之喜爱诗词也是出于天性,而初识先生大名,是在高中偶然读到《唐宋词鉴赏辞典》的时候。但那时我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有朝一日自己竟然能够忝列门墙,成为先生的亲传弟子。即使我后来考入南开大学,在历史系读了七年,而先生就在隔壁中文系任教的时候,我也还不敢有此奢望,甚至连登门拜谒先生的勇气都没有。

叶嘉莹先生,摄于2003年10月(侯艺兵 摄,祝晓风 供图)
然而冥冥之中的一切遇合真是自有因缘。就在二〇〇一年我生日的那一天,一个奇梦彻底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那一天凌晨,我梦见自己站在水边,忽然水中一条大蛇朝我疾速游来,近身之际又冲天而起化为一条龙,盘旋数匝之后,又化为凤凰飞舞天际,最后又化为一个婴儿落入我怀中,整个梦境异常鲜明真切。因为实在太不寻常,所以我立刻起床翻检《周公解梦》,书上说蛇化龙飞、凤凰飞舞、婴儿入怀均为大吉之兆,或主有贵人扶助。可是这个“贵人”会是谁呢?不知道为什么,我竟然立刻就想到了叶先生。
因为那时我在南开历史系读研已临近毕业,以我的书呆子个性,自然是要接着攻读博士。但可惜的是,我的硕士导师刘毅先生当时还不是博导,我也就不能继续跟随了。所以当时也颇有些茫然,只是偶尔想到或者可以试试跨专业考文学博士,不过也没有很明确的方向。说来可笑,完全是在这个奇梦的刺激之下,我才有勇气试图跟叶先生联系。于是我把自己平日东涂西抹的一些诗词打印成册,再附上一封信,因为不敢也不知道如何面呈,所以就跑到南开大学东门外的邮局寄给叶先生了。我当时真是年少轻狂,所以在信中敢于如此出言无忌:
小子汪梦川,楚人也,身无长技,惟自幼好古,于诗词之属用心尤多,然未得人指点,率性自为之而已,或亦近野狐之禅。生非其世,学不逢人,此小子平生所深恨者。
小子久慕先生之名,自闻先生执教本校,欲亲聆教诲久矣,然每自忖微贱,终未敢造次拜访。今小子混迹南开历史系已近七载,毕业在即,自思若如今咫尺之间,犹未与先生通消息,则他日更无论矣,此必为终身之恨。每念及此,心辄怅然。故今斗胆投书于先生,非敢谋伯乐之顾以自高身价,实欲一偿夙愿,惟先生察之。
诗道之不传也久矣。先生执教多年,当亦有此感慨。盖方今学问之绝,病在名师既难求,高徒亦复难觅,授受之途既阻,遂至道衰。然江湖之间,必有诗人,特未为人识耳,岂必尽出于中文系哉!小子何人,乃敢作此语者,欲慰先生寂寥之怀耳。
敬奉拙作《洲上集》一部,愿先生勿以浅薄弃之。
当时写这封信,完全就是“豁出去了”,其实根本没有指望得到先生回应,只是为了不让自己将来因为没有行动而后悔罢了。换言之,就当是完成一次大学生涯中的“壮举”而已,所以我甚至没有在信中留下任何联系方式。然而先生接到信之后,不但没有计较我的无知狂妄,还让秘书安易老师向历史系办公室打听我的情况。我至今清楚地记得,当时历史系的那位老师打电话到宿舍找我,以非常激动的口吻问我是不是给叶嘉莹先生写信了。我还吓了一大跳,以为惹出了什么麻烦,但也只能硬着头皮回答说是。那位老师接着告诉我,叶先生让我到专家楼她的住处找她!那一刻,我简直是如在梦中。
之后,我在约定的日子满怀忐忑地到南开大学专家楼拜谒先生。不过我与先生的初次见面并不那么“成功”,因为我向来讷于言,读的书也不多,所以跟先生的交流甚至略有些尴尬。我记得先生问我写诗词有没有家学、有没有老师指点,我都很茫然地说没有,就是自己瞎写。但是先生还是很随和地跟我聊天,并指出我那些诗词的不足,最后亲笔题赠我一本《顾羡季先生诗词讲记》,更准许我参加她给研究生们开的课。此后如果课程有临时变动,或者有不定期的讲座,先生也都不忘让安老师通知我。所以其实我在还没有入先生门下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亲沐先生之教泽了。

叶嘉莹先生,2003年10月摄于天津南开大学西南村(侯艺兵 摄,祝晓风 供图)
先生给我们开课,往往就我们选定的研究方向或者大家共同感兴趣的问题量身定制。先生总是教导我们一定要打开眼界,不能仅仅局限于诗词甚至文学而已,所以课堂上的讨论不拘一格。记得我入门之初,叶先生曾给我们开课讲陶诗。那时候我还不清楚先生是那么喜欢陶渊明,加之我生性倔强,所以课后写了篇作业,题为《让陶》,把陶渊明狠狠批了一通,大意云:一、中国文人往往有志大才疏之病。其实文学之才不等于济世之才,而文人每不自知,往往自负不凡,以为能治国平天下,实则大事做不来,小事不愿做。以陶传所载,实在看不出他有何政治才能。二、渊明之仕,为亲老家贫犹可,为官田之米可以造酒则不可。而其嗜酒无度,已完全为物所役,何得言高明?至于“不为五斗米折腰”,不过欺来人之名微职卑耳,亦未见高尚。君不见其屡屡“为五斗酒折腰”乎?三、渊明徒为己计,既无政治责任感,亦无家庭责任感;既非良臣,亦非良夫良父。自私如此,还说什么“但恨邻靡二仲,室无莱妇”,更写诗责备孩子没出息,实在太过分。最终的结论是:渊明仕隐无常,仕不能尽职牧民,隐不能自食其力,复图一己之名、纵一己之嗜而不顾妻子,有何高处?!
我不知道先生看到这篇作业的时候是什么感受,但下次上课,先生并没有生气,更没有批评我,而是笑着说了一句话:“梦川以后一定是个好丈夫、好父亲。”当时大家也都一笑而过,至今还传为我们师门佳话。可是现在想起来,我的这篇小文触动了先生的某处隐痛也未可知,不由得为我当年的鲁莽而追悔莫及。更过分的是我在课堂上的表现,有一个同门师妹曾私下提醒我说:“师兄你知道你上课时是什么样子吗?先生在那里讲,你在这里皱着眉,还摇着头!”她还学我的样子给我看,当时我真是吓了一跳:“啊?我真是这样吗?”因为我真不知道我竟然有这种下意识的动作和表情,而且表现得如此之狂悖!但是先生从来没有因此敲打或责罚过我。
我性格上还有一个极大的弱点,即自恃小聪明而很不努力。也因为如此,我第一次投考先生博士的时候,自以为十拿九稳,但最终名落孙山,而且在我最自信的“中国古代文学”这门公共课上考了个不及格。这件被我引为平生奇耻大辱之事,没想到在先生眼里竟然成为“矢志向学”的正面话题。她曾不止一次对门下弟子说,你们看梦川,他第一次没考上博士,也不去找工作,而是继续读书、继续考。后来我读博读了四年,也就是延期一年毕业——其实当时我如果像其他同学那样努力,应该也能够按时毕业,但是我不愿意过得太累,因为觉得不值得;不但自己不努力,我甚至还公然向师弟师妹们灌输“快乐读博”的“有毒”思想。但同样没想到的是,这件事竟然也被先生树为正面典型——梦川做学问精益求精,为了写好毕业论文,他宁愿多读一年!
其实现在想一想,我之延期毕业,除了个性疏懒之外,或者潜意识之中也有不愿意离开先生门下的原因。也有人对我说,可能先生是在用一种特别的方式督促我吧?这也不无道理,因为先生这么当众夸我,我确实是有些心虚汗颜(但我也只敢对同门坦白事实而已,况且我也没有因此而“发愤”)。不过我还是认为,叶先生是非常简单纯粹的人,如果她要批评某个弟子,一定就是很直接地批评,不会用这种曲折的心思。所以我认为先生真的就是这么想的,因为一来她待人宽厚,不愿意把别人往坏处想;而且她自己毫无功利之心,所以我的疏懒、不努力在她眼里也成了不谋功利的“闪光点”。

作者与叶嘉莹先生合影,摄于2007年12月23日
转眼之间,第四年也快过去了,我也即将博士毕业,找工作的事迫在眉睫。我深知先生对这类事情完全没有概念,所以也没有向先生开口求助,而是自己到处撒网投简历,记得我当时还曾联系中山大学的景蜀慧教授,希望跟她做博士后——景老师是叶先生跟缪钺老先生当年在四川大学联合培养的博士,我们也都喊她“师姐”。不过后来找工作的事出现转机,我也非常幸运地留校了。也许这是上天垂怜我和叶先生的这段师弟因缘,所以还要让我继续跟在先生的身边吧。
在先生身边的日子非常平静和充实。先生依然每年招收学生,我也还像之前一样,跟这些一拨又一拨的师弟师妹们一起上课,成为“铁打的师兄”。先生年事愈高,有些日常的杂事也都找我帮忙处理,例如网络断了,电脑出问题了,打印机有毛病了,等等。留校之初,我特意在学校附近租了房子住,所以基本上都能随叫随到,跟先生的关系也愈见亲近。先生对有些花粉(比如香水百合)过敏,但是很多人都不知道,所以往往有客人带着大捧鲜花来看望先生,先生当然表示感谢,但等客人走后就会让我带回家,每每说是“借花献佛”——因为先生知道我对佛学颇有兴趣,曾经有一段时间在家中供佛。到我成家以后,虽然住处远了些,先生有事还是会叫我去她那里。记得二〇一五年的中秋节晚上,先生有事找我,处理完之后已经很晚了,先生就对我说:“很抱歉,耽误了你和家人团聚的时间。”又说:“我这里有些别人送我的月饼,我也不知道是什么馅的,你随便拿一盒回去吧!”我说好啊,正好“归遗细君”,先生听了也笑着连连说好。在骑车回家的路上我还口占了一首打油诗:“良宵谁分作离人,月亦多情暂隐身。归遗细君何物好,先生赐饼不知仁。”这里“归遗细君”用东方朔的典故,“仁”则指月饼馅。我虽算不得“吃货”,但是这种“分甘”之赐的确从先生那里领受过许多。

作者与叶嘉莹先生合影,摄于丙戌除夕(2007年2月17日)
更令我记忆犹新的是,先生往往在不经意的闲谈之中,给我以深深的震撼。例如她曾不止一次对我说,人不能满足于做“自了汉”(略近佛家所谓“小乘”)——我想先生也许看出来我有点这个倾向,所以才婉言告诫吧。还有一次先生更对我说,人生在世,总会有些不得不做的事。假如你不做这些不愿意的事,可能另外那些你想做的事就什么也做不成。就这么简简单单的几句话,其中的深意却令我愀然动容。盖先生饱经忧患,对政治也素无兴趣,但这并不是说先生高居象牙塔,对什么都不关心。其实先生心里是非常清醒的,也深知说话容易、做事情难,所以对很多人、很多事都抱着极大的宽容。正如《离骚》所谓“不吾知其亦已兮,苟余情其信芳”,她只想做好自己力所能及之事,如此而已。先生也常常对我们说“士当以天下为己任”,在我看来,她之以毕生精力推行诗教,就是她所认定的“己任”。所以在先生九十寿庆的时候,我在寿启中写道:“秉无生之澈悟,知其不可而为;兼有待之深衷,尽我所能以对。”自以为颇能道出先生之“弱德”。鲁迅先生说过:“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生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以此衡之,则先生可谓“埋头苦干的人”,其传承、推广中华文化之用心、之努力、之成效,早已为世人所共知,难道这还不算“士”之情怀与作为吗?
当然我和先生之间也并非从无“芥蒂”。二〇一五年,我以博士论文为基础写成的《南社词人研究》一书将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出版社那边照例问我,是不是请叶先生写篇序文?我当然知道这意味着什么,但是考虑再三说还是算了吧,先生现在九十多岁了,做事又一向认真,我这本书六十多万字,她看下来再写序,那得多费劲啊!出版社方面也表示理解。但万万没想到的是,我这种自以为体贴的做法却遭到先生的批评。书出版以后我送给先生看,先生当然很高兴,可是过了一会儿先生就责问我:“为什么你没有找我写序?”我说:“怕您累着。”先生有些生气地说:“有些莫名其妙的人找我写序,我当然不想写;但是像你这种,我是可以写的!你不要觉得是在为我着想……”我看到先生是真有些不快了,连忙“讨好”地说:“那等我以后出诗集了,一定请您给写序!”先生神色这才缓和下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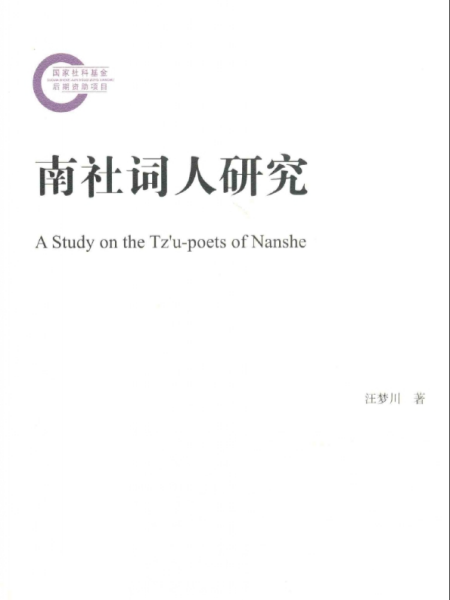
《南社词人研究》
两年后,在朋友们的帮助下,我的诗文集《没名堂存稿》真的要出版了。我也如约向叶先生求序,先生非常痛快地写了,开篇即云:
万事各有因缘,汪君梦川当年以一奇梦而入我门下(详见其博士论文后记),于今已有十五年之久。犹忆当时我在南开大学成立中华古典文化研究所,开始招收博士生以后不久,一日忽然接到自本地邮局寄来的一封极为厚重的信函。启封之后,才知是一卷诗稿。而函内并无片言只语之说明,只在卷尾署名曰“南开大学历史系汪梦川”。展读之下,乃颇使我有“惊艳”之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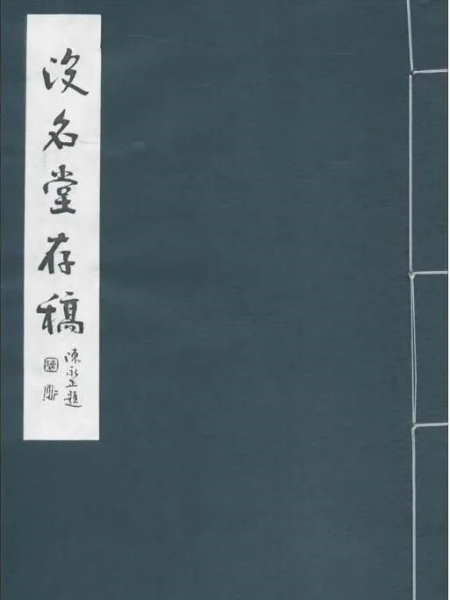
《没名堂存稿》
接下来先生对我不吝大加称赏,倒真是有些“溢美”和“过誉”了。先生在序文里还说:
汪君今日既配嘉耦,更喜获麟儿,故其所作乃于一贯的感时伤事之史笔以外,更另添了一份室家之乐的情趣。而其长达六十余万字的《南社词人研究》之巨著,亦已获得国家社科基金会之资助,于近日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刊印出版。诸喜临门,壮途方始,则其未来之成就,必将更有可观者也。书此致勉,企予望之。
我读到这里,总觉得先生似乎还对《南社词人研究》作序之事“耿耿于怀”,真是令我感愧无地!先生还特别说道:
最后我还更要对汪君表达一份谢意。盖自去岁之秋,南开为我既举办了九十寿辰之庆祝,更于同时举办了“迦陵学舍”落成之典礼,举凡典礼中之一切文字,自贺柬之文启以至于学舍之题记,并皆出于汪君之手笔……而我于此耄耋之年,乃能得见门下之士有如此之成就,其欣喜感激,盖更有言语所不能尽者……

叶嘉莹先生90岁生日,摄于北京

迦陵学舍题记
行文至此,木讷如我,也不由得泫然欲泣。我自忖不过区区一狂生而已,果有何德何能?而先生对我竟如此之垂青、如此之期待;再反观自己这些年来的蹉跎沉沦,实在愧负先师二十余年的栽培之恩了。
二〇二四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深夜,我开车送先生的女儿赵言慧女士到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商讨将先生转入ICU病房的细节,但是一时没有结果。小慧姐(其实论年龄言慧女士是我们的长辈,但先生一直让门下弟子按传统以平辈相称)不忍心让我在医院久等,就让我先回家了。当时谁也没有想到,这是我见先生的最后一面,我也是先生的弟子之中最后见到先生的人。二十四日下午,我收到一位同门发来的微信,询问先生是否过世了。我还回答说“你听谁说的?我昨晚还去看先生了,没什么事啊”!但是我心里也有点不安,立刻致电有关方面询问,确定先生是真的过世了!听到噩耗我并没有流泪,只是有些手足无措,甚至还有些莫名的愤怒。又过了一会儿,文学院的李锡龙院长给我打来电话,让我代作一副挽联。我很快就写好了,因为对我来说,先生之生平与成就如日月之光明历历在目,所以我写得坦然无碍,甚至不怎么需要斟酌考量。我写的挽联是:
一老证斯文,从忧患修来,作词中仙、天下士;
百年闻至道,守孔颜乐处,是仁者寿、圣之时。
上联“一老”语出《左传·哀公十六年》孔子去世后鲁哀公所作诔辞“旻天不吊,不慭遗一老”;“证斯文”者,则以先生之生平而言,大可谓为“天不丧斯文”之象征。“从忧患修来”则本于王国维《人间词话》“天以百凶成就一词人”之说,先生饱经忧患,自不待言;而所谓“修”者,则谓此为先生之修行也。“词中仙”即词仙,语出姜夔《翠楼吟》词句“此地宜有词仙,拥素云黄鹤,与君游戏”,既肯定先生学术(尤其词学)之成就,又隐“驾鹤”之意。“天下士”意指才德非凡之士,语出《史记·鲁仲连邹阳列传》:“始以先生为庸人,吾乃今日知先生为天下之士也。”以先生之功业作为,自无愧于天下士之誉。
下联“百年”语带双关,一指先生期颐之寿,一则婉称先生仙逝;“闻至道”者,盖先生平生最仰慕孔子,更常以“朝闻道,夕死可矣”自励,如今可谓功德圆满。“孔颜乐处”亦出《论语》,谓孔子、颜回皆能安贫乐道。先生曾屡屡告诫弟子:“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她自己也一向自奉甚俭,于饮食从不讲究;在公众场合适当讲究衣着,也是出于对自己、对他人的尊重,因为若刻意效法公孙弘之布被,反倒有些虚伪了。所以先生衣着也以素雅洁净为尚,从未在意名牌。“圣之时”则是孟子所谓四种圣人之一,特指孔子,谓其能顺应时势之变化而为进退。
如今我已无法知道先生若看到这副联语会是什么反应,但是去年我在先生百岁寿庆时写的一副贺联,我知道先生看了很满意:
浮四海肯赋归与,自守诗词家国;
历百凶欲追来者,独交天地精神。
上联写先生自海外归来,以诗词为终身事业。“归与”出自《论语》:“子在陈,曰:‘归与!归与!吾党之小子狂简,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下联谓先生饱尝艰辛,而老当益壮,境界日高。“追来者”亦出《论语》:“楚狂接舆歌而过孔子曰:‘凤兮!凤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独交天地精神”则出自《庄子》:“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而不敖倪于万物。不谴是非,以与世俗处。”我自信这是先生之传神写照。当年曾有人问先生:“孔子说‘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您现在快九十了,那该是一种什么境界?”先生微笑答道:“庄子说过‘独与天地精神往来’,我是希望如此的。”先生如今或者正在“藐姑射之山”与天地精神往来吧!

叶嘉莹先生,2005年摄于清华大学
我为先生写的联语,的确总是自觉地处处以先生比拟孔子,有人以为“过誉”,我却认为先生完全当得起。盖先生毕生以教师为第一身份,以教育为第一事业,亲炙弟子之中有出家人、有艺术家;有学哲学出身、有学法学出身、有学物理出身;有早已知名的教授,也有尚在冲龄的儿童;有小学生、中学生、大学生,以至硕士、博士、博士后;有黄种人也有白种人。若论有教无类、弟子之众,以及执教地域之广、时间之长,实在都已远超先圣,真可谓“广大教化主”。更何况“吾爱吾师出至诚”,我所写即为我所想,又何过之有?!
原文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k9RnPsEmxFk5A1n1HWyfJ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