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文以平实笔触回顾了作者学习俄、英、日三门外语的经历以及治学《柳宗元传论》过程中的遗闻逸事,这是对作者人生走向具有重大决定意义的两件事,描摹出作者在艰难环境下的潜心学问的历程。
忆旧二则
孙昌武
本文刊登于《随笔》2024年第2期
|学外语|
工作过程中有时候要填写履历表,其中“外语水平”一项,我一般填写“粗通俄、英、日语”。这是我外语水平的真实情况,这也是因为我没有正规地学过任何一门外语,所以三种外语,“读”的能力相对都高些;“说”则是只能简单地对话;“写”则基本无能为力(后二者三种外语程度不同)。
父亲去世后,我随母亲到了北京,那时小学、中学学的是俄语。一九五一年上中学,正值中苏友好的“蜜月时期”,许多俄国作家的作品译成中文。我酷爱文学,虽然只是个中学生,读得真是如饥似渴。学外语有个规律,入门以后的一段时间会进步很快。当时北京王府井国际书店买进口的原版俄文书很便宜,我想读俄国作家的原著,就买一些,试着借助字典阅读,很快就提高了阅读能力,能够大体上读懂了。我知道有人通过翻译外文作品来学习外语,有一次我买到一本文艺理论书——别里索夫的《巴甫连科的创作道路》,读下去觉得很容易,突发奇想:何不试着翻译出来。于是就给上海新文艺出版社写信表示想翻译,不承想不久收到回复:“同意”了,让我“试译”一万字。我翻译好了寄过去,很快收到约稿合同:一年内交稿,稿费千字八元。这稿酬是相当高的,当时一个工人的月薪大概三十元。当时手头能利用的工具书只有一部简单的《俄华词典》。我又找了日本战前出版、盗印的八杉贞利的《露和辞典》(借助其中的汉字注释)和在国际书店买的原版四卷本乌沙科夫《俄语词典》参考。我利用高二一学年的课余时间译成全书,交出版社。

《巴甫连柯的创作道路》孙昌武 译
出书时已经是我上南开的次年秋天了。当时,正值“反右”斗争高潮,我在北京一中的同学、好朋友张祖荣被《中国青年报》的社论点名,定为青年学生中的“右派分子”。大家知道我和他来往多,让我谈对张的认识。我说他是品学兼优的好学生,政治上要求进步,不是右派,并在大会、小会上和大家争论,于是成为众矢之的。起初,在班级团支部受到批判,但我坚持不承认“错误”,继而在全系大会受到批判,最后被打成“阶级异己分子”,开除团籍。《巴甫连科的创作道路》的出版,客观上对我当时的处境产生两方面影响:一是因为中学生就能翻译一本外文书,表明这个年轻人很努力,聪明好学,因而在对我的处理上就慎重些,没有立即打成右派;另一方面,接着“拔白旗”、批“白专”,这又成为我的“罪状”之一。
进南开后通过考试,我第一外语俄语免修,选修第二外语英语。当时中文系英语选修课只有中级班,选修的都是四年级学生。我插入这个班,可我连英文字母都没学过。上的第一课是法国作家都德(Alphonse Daudet)的The last lesson(《最后一课》),接着是法国作家莫泊桑(Henri Maupassant)的The necklace(《项链》),等等。上第一课,课堂上十几个人,老师先让每个人起来念一段课文。应当是考查学生水平,叫到我,我说不会。老师以为我腼腆,不敢念,说不管怎么样你试着念。没办法,我就按俄文拼音的方法念,惹得哄堂大笑。我就这样勉强跟着学,也就逐渐学下去。四年级的班长叶雪芬,一句一句教我念课文,对我帮助很大。她毕业后被分配到湖南师大,做杨树达的助手。不久,我就跟上进度了,只是说和写一直不行。后来我坚持自学,没有合适的课本,我就找苏联出版的、给他们中学生编写的英文课外读物,借助俄文注解,读了缩写的狄更斯《双城记》、柯南·道尔《福尔摩斯侦探案》以及丹尼尔·笛福的《鲁滨孙漂流记》等。到英语班结业,通过了。
接着上四年级,我又报名选修第三外语日语。我学日语是和北京一中的同学袁梁林的一段交谊有关系的。袁梁林是东北奉系军阀张作霖的亲信、后来成为汉奸的袁金铠(1870—1947)的儿子。袁金铠早在张作霖担任北洋军阀奉系陆军二十七师师长的时候就投其幕下,后来成为张的第一代军师;一九二八年“皇姑屯事件”、张作霖被日本关东军谋杀后,他担任东北临时保安委员会副委员长,委员长是张学良;再后来在伪满洲国担任内务府大臣、哈尔滨特别市市长等要职,一九四七年去世。我和袁梁林做同学的时候,他家住东城交道口附近一个胡同的小院里,其母是东城区政协委员;有个哥哥,有精神病,不是暴躁型那种,但近距离接触也挺吓人的。他哥哥伪满时期在长春(当时称“新京”)大学读书,和后来成为日本著名中国学家、被称为当代日本中国研究第一人的竹内实(1923—2013)是同学、好朋友。大概是一九五五年,竹内实作为翻译陪同日本一个民间贸易代表团来华访问,求见袁梁林的哥哥,当然不便,不让见。袁梁林的母亲去见了面,他给留下礼物,是一个很漂亮的皮包。我托袁梁林的母亲代为传达想学日语的愿望,竹内实回日本后寄来一些学习初级日语的教材。当时我不可能花大力气学,但总算学了些字母等知识。
上大学后我又知道日本的中国学研究水平很高。当年学校开设法、德、日等各种外语供选修。我英语通过后选日语,全校选修日语的只有六个人,教师是抗战时期曾在延安工作的日本人泽田先生,其丈夫当时是某大学的领导。她家住校内,我们到她家上课。她坐床上,我们六个人坐在床边或凳子上。她本来不是教书的,不懂什么教学方法,和我学英语的办法一样,教过字母就念文章。第一篇念的是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她念一句就让我们跟着念,接着让我们背,然后讲点文法。课堂很活跃,经常聊天。她当年在日本念大学学的也是文科,善俳句。据她自己说达到相当水平,她曾拿出日本早年登载她作的俳句的刊物给我们看。她和我们聊天夹杂着日语,我们也就跟着学了些常用口语会话。这样学了一年多,我的日语算是打下点基础。
离开南开后,不管所处环境如何艰难,我都没有放弃继续学习外语,总是设法找些英语、日语读物、资料看。即使在“文革”时期,在营口接受“改造”,那时候邮局能订到外国“左派”刊物,英文的Guardian,日文的《毛泽东思想研究》,虽然家里经济条件很紧张,还是订了。好在也都非常便宜。借助这些,也就进一步提高了阅读能力,达到填写履历表“外语能力”一栏“粗通俄、英、日三种语言”的程度。当初绝没想到这对于我后来做研究工作大有用处。特别是日本学者的佛教研究可说是执全世界学界牛耳,我研究佛教,汲取、借鉴他们的研究成果不少。以后有机会到各国讲学、访问,又利用这几种磕磕巴巴程度的外语,起码问个路、找个酒店乃至办个什么手续、填个什么表格等没有问题,不必劳烦接待方找人帮忙翻译,也让人家省事不少。
|柳宗元帮我大忙|
考上大学,我读中文系。系主任是著名的鲁迅研究专家、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学科的奠基者李何林先生,开学后第一次做报告,先生就对我们明确:中文系不是培养作家的,是研究中国语言文学的,所以,大家要按学者的方向打造自己,早些选择确定自己研究方向。李何林先生的话在同学中引起很大反响,一些已经是小有名气的作家同学,听了这番话大失所望,有的甚至干脆退学了;而我和另一部分同学则大受鼓舞,踌躇满志。我酷爱古典诗文,在中学时就读过《古文观止》《唐诗三百首》等古代文学选本,对古代文学产生浓厚兴趣,特别喜爱唐代韩愈、柳宗元的“古文”,从那时起就立志从事古代文学研究,又以唐代文学作为主攻方向。
一九六一年大学毕业,因为我是“阶级异己分子”,又受过处分,被分配到辽宁营口农村当农民,接受“劳动改造”。就在教育局人事科长给我开去农村的派遣信的时候,碰上营口师范学校缺教师,校领导到教育局要人,听说来了个大学生,就硬把我“抢”了过去。现在回想起来,人生真是奇妙:如果校领导晚来一分钟,我可能就拿上派遣信下农村了。就是这样的机缘巧合,我到了辽宁营口师范学校教语文。这样,我就有了一个相对安稳的环境可以继续我的学习和研究。因为是“戴帽”身份,要老老实实接受“监督”和“改造”,平时除了教书我就认真读书,读我手头有的唐人集子。“文革”开始家被抄了,许多书被“造反派”抄走了,所幸漏掉一些,包括我正在研读的《柳河东集》,使我得以继续研究柳宗元。
 《柳河东集》
《柳河东集》
“文革”十年,大运动套小运动。后期有一段“批儒评法”运动,里面又包括“读《封建论》”“批《水浒》”等内容。赶巧的是《封建论》正是我一直着力研究的柳宗元的一篇重要文章,其主题是讨论历史上郡县制与分封制的优劣。柳宗元给这个长期争论的问题做了总结。我研究柳宗元,当然对着文章从文字解释到思想内容、写作技巧上,都做过认真、详细的探讨。可是当时号召读《封建论》,一般人却对它少有了解的,市里甚至没有多少人知道,包括市领导也找不到这篇文章。后来《封建论》赶印出来了,因是古文,难词难字很多,一般人读都读不下去,遑论理解。过了一段时间,许多工农兵写作组、大批判组编写出各种各样的注释文本,但对于一般人来说读起来还是困难重重。但是有“最高指示”,读,乃是必须完成的神圣任务。这样,我就意外地得到了“用武之地”。
因为学校里的人都知道我一直在研究柳宗元,还在《文史哲》上发表过研究文章,于是被“请”出来讲解《封建论》。先是在学校里给师生讲,消息很快传开,市革委会干部要学习,也请我去讲。随着听讲范围不断扩大,就给更多单位、更多干部讲。有一次搞得形式相当隆重,在市政府大礼堂讲,听众是市革委会各机关和市属各单位领导干部。柳宗元这篇文章讨论历史上“封建”制与郡县制的优劣,表达了作者反对藩镇割据、维护国家统一的进步政治主张,阐述了具有重大理论和实践意义的历史发展观念。柳宗元的文章风格历来以“清峻”著称,在古代作家的文字中算是相当艰深的,《封建论》讨论的又是相当复杂的理论问题,阅读和讲解确实不容易。我已经当过几年教员,懂得讲课要照顾听众水平,在讲解时从细致解释作品词句入手,一步步引导听众理解其中说些什么,进一步讲解其理论内涵。我讲解中又尽可能表述浅俗又有点趣味。我在台上讲,大多是在大礼堂,看见下面上千人静悄悄地听,知道效果不错,更增添了讲解的兴致。这样,经过一段时间,我讲《封建论》在全市也就有相有名气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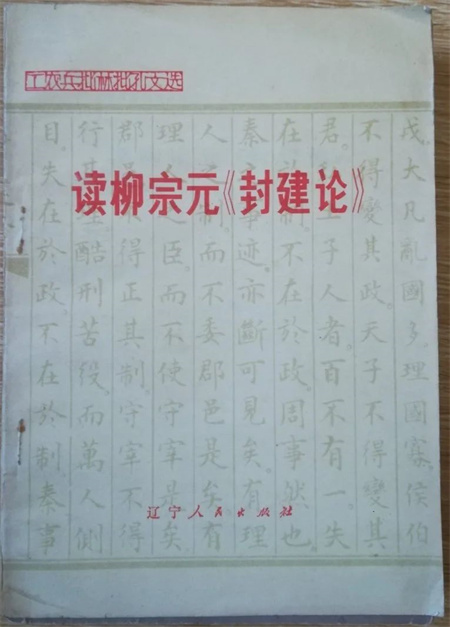
20世纪70年代学习《封建论》的资料
时值“文革”时期“三支两军”,市革委会主任是解放军的一位师长。他听过我讲《封建论》,驻在附近大石桥镇的他所属军部官兵也要读这篇文章,就把我推荐给军部,军部派车到家里把我接去讲。到军部,由一位副军长接待,对我说了许多感谢、勉励的话。后来我知道这位副军长姓李,据说原来是新四军的,曾在上海念过大学,文科出身。讲课在晚上,李副军长陪着我进入讲课大礼堂的时候,全场上千官兵起立、鼓掌。李副军长告诉我讲课对象是全军团级以上干部。台上几位军首长列坐,台下军人整齐端坐,一派肃然,这又给我极大激励。我还从来没有经受过这样隆重的大场面,顿时感动至极,深深意识到责任重大。全场认真听我的讲解,讲完后,掌声雷动,让我激动得不知所以。
讲完了,李副军长送我,等车时闲聊,对我说:“我们党就是需要像您这样的‘又红又专’的知识分子啊!”听了,真让我不知道怎么回答。营口市里大家大都清楚我的底细。但让我来部队一个军的领导机关讲课,本来心里就打鼓,有点“欺世盗名”的感觉。听了这样的夸奖,发觉对方显然不知道我的“戴帽”身份,可是又不能不回答,我只好如实“坦白”了。我说:“您还不了解,我得把我的情况汇报一下。”接着我大致说了在大学受处分来到营口,现在还是接受改造的身份。李副军长听了,十分惊讶,连说“这怎么可能”,又问这些年是否还有什么别的问题。我答说没有。他说:“我了解一下吧!如果没有什么大问题,这么些年了,也该解决了。”就这样,我不知道事情后来是怎么运作的,总之不久以后,省里就发来调令,调我到省人事局“另行分配工作”。我知道当时辽宁省革委会的领导也是这个部队的,估计省人事局发出这个调令是李副军长起了作用。
想一想,如果没有毛主席发动“批儒评法”;再追溯一步,如果毛主席不是对古籍那么爱好、在他发动的运动中时时运用古籍名句作为斗争手段;又如果“批儒评法”没有把正是我所熟悉的《封建论》作为重要内容,总之没有这些机缘,也就不会让我这个接受改造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由于讲《封建论》而出了名,继而也不会有和部队首长交往并得到他关照,从而得以“平反”的机会。部队首长对一个普通知识分子的关心和爱护更让我永志不忘。
也是与柳宗元研究有关,使我有机会结识日本著名的中国学家清水茂教授,对我开展国际学术交流起到很大作用。人民文学出版社接受书稿《柳宗元传论》,是在“文革”结束之后不久。当时出版社准备出版的书稿不多,往往请作者到北京、住在出版社的招待所里改稿。天津离北京近,我在学校里又有课,京、津来往方便,需要商量、修改书稿,当天来取,看完了再送回去。这种往返又让我得到一次机遇。

《柳宗元传论》孙昌武 著
我记得那是一九八〇年夏某天下午,我到的时候刚刚是午休过后,编辑们在收拾办公桌上的东西,像是准备出去。有人告诉我下午有几位日本专家在北师大讲演,说研究书稿是不可能了,如果有兴趣可以跟他们一起去听听。我当然愿意去,就乘社里的车跟着去了北师大。记得是三个日本学者讲演。其中一位是小南一郎,讲什么内容忘记了,后来和他交往几十年,直到如今。另一位是清水茂,京都大学教授,久闻大名,他的论文《柳宗元的生活体验及其山水记》曾发表在《文史哲》杂志一九五七年第四期,后来收录在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的《中国古典散文研究论文集》里,是新中国成立后介绍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古典文学成果较早的一篇专题论文,我在大学读书的时候已经读过;后来写《柳宗元传论》,在相关章节里也曾借鉴其中的见解。这次有机会见到他,感到很幸运,我们以后也一直保持交往。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我执教神户大学的时候,曾到京都清水茂的研究室拜访过他,接受他的招待。八十年代末我担任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外国人研究员,他是京大文学部部长,有幸又有同僚之谊,更密切地交往过一段时间。
那一次他在北师大讲演,十分凑巧,讲的是日本所存《柳宗元文集》三十卷本残卷情况。我研究柳宗元,写《柳宗元传论》,当然知道当初柳宗元好友刘禹锡编辑《柳宗元文集》三十卷,但这个文本早已佚失,具体面貌后世已不得其详(前几年这个文本在日本东京神田神保町的一家书店里发现,曾在门下进修的户崎哲彦君有详细报道发表。据说该书索价两亿日元)。清水茂讲的这个三十卷本残卷收藏在陆心源的《皕宋楼丛书》里,整个丛书在清末卖给了日本人,如今存放在东京《静嘉堂文库》,该文库属西武财团所有。残卷只有几页,主要是残佚的目录,从中可窥知那个三十卷本原貌点滴。当天三个人讲演,清水茂讲的这个主题听众反应十分冷漠。因为绝大多数人并不知道这个文献史上的细小旧案,更难以理解讲演者研究成果的价值。但我听了十分兴奋。会后我冒昧地向清水茂请教。这大概也很出乎他的意料,他耐心、亲切地回答了我。我又冒昧请求他给我一份这个残卷的影印件。他慨然应允,回国不久就邮寄来了。有了这个影印件,使我得以补充我的书里关于柳宗元文集版本的论述;又征得清水茂的慨允,把这个残卷的一页作为书影放在《柳宗元传论》卷首。
一九七九年九月,我奉调回南开大学,立即整理在营口十九年坚持研究柳宗元积累的文稿,成三十万字的《柳宗元传论》一书,交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八二年八月出版。当年国内还出版了社科院文学所侯敏泽先生著《中国文学思想史》,拙作和这本书一起,被认为是“拨乱反正”的实绩,受到国内外广泛关注和好评,对我之后的学术生涯起了重大促进作用;清水茂主持的《中国文学报》又为拙作发表了一万五千余字的长篇书评,给予高度评价。后来清水茂又介绍他的两位弟子川合康三和户崎哲彦来我门下留学;我作为客座教授赴神户大学执教,也是因为得到他的推荐。
一九八三年,天津市第一届社科优秀成果评奖,当时还没有个人申报制度,不知道为什么《柳宗元传论》被评为一等奖。我调回南开,当时按天津市户口管理办法调入者必须具有高级职称才能带家属。但是我在营口不可能取得职称,南开人事处专门给市人事局打了报告才得以批准。有了这部专著,我到校两年就越级评为副教授,这样才有一九八四年初作为客座教授赴日本的可能。
从一九五七年我接受批判、“戴帽”,二十余年间被隔离在学术活动之外,又羁束在一个小城。而《柳宗元传论》由一个国家级出版社出版,我作为突然“冒”出来的一个新人,自然受到出版社、杂志社注意,陆续发表文章、出书,接下来的几年是我学术论作丰富的时期,包括我开始研究的佛教与文学关系课题,也是那段时间打下的基础。
这样,题目说的“柳宗元帮我大忙”,实际是我克服困难、坚持柳宗元研究终使我一步步改变命运,学术活动走上坦途。因为尽管我个人受到打击,身处困境,“文革”时期学术研究活动基本停顿,但我始终坚信:中国这样的文明古国、新兴大国,是需要文化支撑的,为文化建设努力会功不唐捐的。这样的信念毫不动摇,我也就能够在艰难的生活环境中、栖居在陋室里把研究工作坚持下去。
审核:韦承金
|